吉普赛:来自秦特或阴特的黑人故事

1.你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是一个奇怪的、在这颗星球上称得是上独一无二的民族:没有固定的家、家乡、祖国的概念,常年流浪,赶着吱吱嘎嘎的大篷车队,越过千山万水,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国度到另一个国度;天性豪放不羁,热情勇敢而又狡黠;对拐骗说谎偷盗甚至杀人越货之类的行为少有廉耻感,但在夫妻家人及同族人之间却乐于互助,社团结合非常紧密;习惯于餐风露宿的浪游生活,却又谨守婚姻家庭的约束;女人们看相算命、卖艺求乞、贩卖来路正当或不正当的药品,男人以作马贩兽医、剪骡毛补锅等为生……没有专属自己的宗教(常以居住国的宗教为宗教),也不大用本民族语言(操当地语言甚至比使用自己的语言更流利),因为没有文字,缺乏相应的历史记载,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80岁的吉普赛捕鱼人
大篷车
主提琴手在演奏
吉他手在演奏
塔罗牌玩家
飞行的吉普赛人
“只有圣明的上帝才知道我们来自何方,而他又是那样的虚无缥缈,以至于无法将真相告诉世上的人们。”
一位英国吉普赛人查利•史密斯如是说。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这是一个只存在于传奇想象和文艺影视作品中的民族。对其历史文化与种族身世,长期以来都莫衷一是:一种观点认为这些人原籍南非,可他们声称埃及才是自己的祖国;东方研究专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吉普赛人原本生活在印度北部,因突厥人入侵,于10世纪左右离乡背井,一部分从波斯、土耳其进入南欧,另一部分经由亚美尼亚、俄罗斯迁往东欧……他们来到西欧的时间则要更晚一些了——
公元1417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德国小城卢尼堡突然出现了一队形貌奇特的异族人:骑在高壮骏马上的首领手牵猎狗,装束华丽,身上佩戴着光彩夺目的银饰,大群衣衫褴褛的青壮年男子紧随其后,压阵的是装载妇女儿童的大篷车。两位首领自称是来自“小埃及”的“公爵”与“伯爵”,在向市政当局出示了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格斯蒙德签署的优良品行推荐信后,凭借三寸不烂之舌,通过自述无从查考的不幸遭遇,他们赢得了当地人的同情与资助,然后得以继续漫长的旅程。1418年,这群人经过莱比锡和法兰克福,次年进入瑞士,沿途都无一例外得到了帮助施舍。1422年夏,他们抵达意大利的波伦亚和罗马,并取得了教皇马丁五世的信任……自十世纪始至今,这一特殊人群已遍布西亚、北非、欧美等地。
吉普赛女郎
罗马尼亚吉普赛人
“吉普赛人”(Gypsy或Gypsies)是最为通行一种的称呼——它源自“埃及人”一词(Egyptian)——这个以讹传讹的称呼本身已经表明了我们的无知(因其跟北非的埃及人毫无瓜葛)。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个民族尚有多达数十种五花八门的名称:如茨冈人(俄罗斯)、吉塔诺人(西班牙)、波希米亚人/吉当人/齐果纳人(法/德/东欧诸国)、鞑靼人/摩尔人(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扎拉西人(波兰)以及齐热内尔、赛利斯人等等。如果说“吉普赛”是世界上名字最多且最变换不定的民族,这其中恐怕是没有什么夸张成分的。
2、“从秦特或阴特来的黑人”
远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乔治•博罗——一位传教士兼旅行家依据他长期接触吉普赛人的经验写成了两本有名的书,一本名为《秦卡里》,意思是“从秦特或阴特来的黑人”,该书的主要内容是有关吉普赛人起源的传说及宗教信仰、礼俗习惯、语言谣曲。之后法国作家梅里美曾参照此书创作了著名中篇小说《卡门》。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学者布雷多克在《婚床》中介绍吉普赛人的婚姻方式时,还参考并引用了前述乔治•博罗的那本书。
吉普赛人的确自称“黑人”,其肤色较一般人深,大而黑的眼睛每每有明显的斜视,睫毛长而浓密,眼光如猛兽(大胆兼畏缩)。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原系印度低种姓——即印度土著黑人、雅利安人与印度矮黑人混血的后裔——公元11世纪,属于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的阿拉伯人入侵后,与印度人保持了长达几百年的杂交,因此今天印度人的外貌具有显著的阿拉伯人特征,而10世纪外迁的吉普赛人则基本保持了印度低种姓人的血统。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所著《猎人笔记》有对茨冈女人玛霞面相神态的精彩描写:
“浅黑色的脸,一对黄褐色的眼睛和一条漆黑的辫子;又大又白的牙齿在丰满红润的嘴唇里面闪闪发光……纤细的鹰鼻和张开的半透明的鼻孔,高高的眉毛的刚强轮廓,苍白而略微凹进的面颊——她的全部相貌表现出一种任性的热情和无所顾忌的勇敢。盘好的辫发底下有两排亮闪闪的短发在宽阔的颈子上一直生向下面——这是血统和力量的特征。……她的眼光象蛇舌一样闪耀着……脸上显出一种又象猫又象狮子的表情。”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俄文名: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 1818-1883)
更典型的是法国小说家梅里美笔下的嘉尔曼:
“她的皮肤虽然很光滑,但是非常接近铜色;她的眼睛虽然有点斜视,但是很大很美;她的嘴唇虽然有点厚,但是线条很好,露出雪白的牙齿……她的头发虽然有点粗,可是颜色漆黑,带有蓝色的反光,象乌鸦的翅膀一样,又长又亮……她的美是一种奇特的野性的美,尤其是她的眼睛,有一种肉感而凶悍的表情。”
电影《卡门》
梅里美手迹
普罗斯佩·梅里美(Prosper Merimee 1803-1870)
老荷兰画派代表画家弗兰斯·哈尔斯名作《吉普赛女郎》凸显的也是人物的率真野性和自由洒脱——从蓬松飘飞的黑发,顾盼流连的美目到脸颊的红晕,俏皮而带挑逗意味的微笑,呈现出一位吉普赛少女某个生活瞬间的神态和行止;笔触接近速写的衣裙皱褶处理,色块组成的非具象背景,近景的半身构图,有如一帧自然随意的日常生活“快照”,颇具还原真实的现场感。
弗兰斯·哈尔斯《吉普赛女郎》
由迁徙不定的生活方式决定,加之有意逃避人口登记与普查,迄今尚无一个可信的吉普赛人口的统计数据——来自不同渠道的总人口数量低至2、3百万,高至1500万。主要聚居在巴尔干半岛、中西欧、美国、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及中东、北非等地——其中罗、保、匈牙利、西班牙和美国的吉普赛人数均超过五十万,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是保加利亚。
跟文人艺术家的想当然相反,这个种族实际上极为珍视肉体贞洁:幼女时期用“diole”(手帕)罩住耻骨区以保护童贞;举行婚礼之前,娘家与婆家要各荐两名女监护对新娘做检查,失贞者有可能被处死;妇女在严格的婚姻规则下对丈夫忠心不贰,却又远离乏味的一致性:宁肯动荡流转浪迹天涯,也不愿意居家守业“平稳”度日;身姿衣着尤其是歌舞表演或会表现得热情狂放以至性感撩人,但那只是为了赚钱养家迎合异教徒心理——她可以拉皮条,却不当娼妇;她唱猥亵小调,却不让猥亵之手沾她——当然因生计所迫的作奸犯科行骗在所难免,否则又何来“魔鬼的门徒”之名呢?
3、“老智者”与“致命女郎”
也许是受人类固有的猎奇心理驱使,更可能是基于出版市场/影剧票房的考虑,几个世纪以来,吉普赛民族及其颠沛流离的“浪漫”生活不断被纳入小说诗歌、绘画雕塑、戏剧影视等几乎是所有文学艺术门类的创作,身为永久的外来者、“低贱”种族而备受歧视迫害的吉普赛人(尤其是吉普赛女性)成了东西方文人艺匠、歌手乐师情感梦游、审美想象及精神意淫的对象。
仅以文学影剧作品中的吉普赛女性角色为例,为大众熟知的就有俄国诗人普希金长篇叙事诗《茨冈》里为爱情而生为爱情而死的金斐拉,法国作家雨果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女主角、美丽善良的埃斯梅拉达,梅里美小说《嘉尔曼》(以及据此创作的乔治·比才的歌剧《卡门》)充满原欲与妖冶之美的“恶之花”嘉尔曼,苏俄作家高尔基短篇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里美得眩目却“不自由,毋宁死”的拉达,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里坚贞不渝、忠于爱情的叶塞尼亚……等等,这些吉普赛女性大多美艳热情、爱情至上同时更热爱自由,焕发出独异的智慧与情感的魅惑力,予人难以捉摸的野性及神秘感。
《巴黎圣母院》女主角埃斯梅拉达
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主角叶塞尼亚
问题的症结在于,文艺作品中呈示的吉普赛世界和吉普赛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不同时代作家艺术家的“集体想象物”:与其说再现了某个民族的真实生存状态,不如说是书写了作者的主观理念和审美认知。吉普赛人富于异质性的生活确实激活了文人艺术家的想象力与创造热情,可吸引慑服他们的往往是其中带有传奇色彩的部分元素:自由浪漫、爱恨情仇、异族情调等,而这个族群困顿屈辱、苦难哀伤的一面反而被有意无意淡化甚至忽略了——当然作者对真实的吉普赛世界知之甚少也是造成这一点的重要原因。
有论者认为,在自浪漫主义始至二十世纪初的各国作家诗人笔下,最引人注目的吉普赛文学人物有两类:一类是作为通灵的先知、巫师的“老智者”形象,以英国作家司各特历史小说《盖伊·曼纳令》(又名《占星人》,1815年)塑造的吉普赛老妇梅格·梅瑞丽丝为代表——作品一开篇就遭驱逐的她,其预言和建议却贯穿全书并一直左右着主人公的命运,且居于族群文化记忆和主人公个人记忆的中心。伯特朗家的老梅格形象鲜明,影响巨大,以至成了吉普赛人的英国式想象的源头之一——司各特的同时代人济慈就以《老梅格是个吉普赛人》一诗对其进行过重写:
“老梅格像玛格丽特皇后一样勇敢/像亚马棕女人一样高大/她身穿一件陈旧的红毡斗篷/头戴一顶破帽。愿上帝在某处/庇佑年迈的骸骨——/很久很久以前,她已安息。”
约翰·济慈(John·Keats,1795—1821)
司各特纪念塔
还有华兹华斯的《行乞人》:
“她像一个高个子男人那般高……她有埃及人的棕色面庞/ 体格够得上成为/统领古老亚马棕兵队的女王/足以当上强盗头子的夫人,在那些希腊岛屿上。”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年)
另一类更常见的吉普赛文学人物即“诱惑者”,或谓“致命女郎”(Femme Fatale直译蛇蝎美人),典型者如前述普希金诗中的金斐拉,雨果创造的埃斯梅拉达,梅里美笔下的嘉尔曼等人。
《巴黎圣母院》中的埃斯梅拉达
更极端的是高尔基的《马卡尔·楚德拉》,那一骄傲的吉普赛青年男女(拉达和洛依科·左巴尔)为了自由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爱情与生命:
“我们还来不及猜想左巴尔想干什么,拉达就已经躺倒在地上了。左巴尔的弯刀齐刀柄地竖立在拉达的胸口上。我们都惊呆了。而拉达拔出刀来,把刀扔在一边。她用自己的一绺黑发堵住刀口,微笑着,响亮而又清晰地说:‘再见,洛依科,我早知道你会这样做的!’……达尼洛捡起那把刀子久久地看着,花白的胡须在颤抖。刀上拉达的血还没有凝固……然后走近左巴尔,把刀插进了他的背部……”
玛克西姆·高尔基
19世纪20年代初,被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流放到南俄的诗人普希金写成叙事长诗《茨冈》,讲述厌倦了城市文明的贵族阿乐哥去茨冈人那里寻找自由的故事——
“一群茨冈人有说有笑/在比萨拉比亚到处流浪/他们搭起破烂的帐篷/今天过夜就在小河旁/多自由自在,在露天下/宿夜既快乐,睡梦也安详……”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命运有点类似嘉尔曼,吉普赛姑娘金斐拉先与他相爱又移情别恋;因为无法忍受对方“愿意爱谁就爱谁”并且“死也爱着”的爱情观,痛不欲生的阿乐哥最后杀死了自己深爱的情人。跟《马卡尔·楚德拉》不同的是,金斐拉的父亲并没有睚眦必报,而是选择了平静的告别:
“离开我们吧,你高傲的人/我们粗野;我们没有法律/我们也不惩罚,也不处刑——/我们不需要流血和呻吟——/但不愿和凶手活在一起……你寻求自由只为了自己/你的声音我们听得可怕——离开我们吧/别了,愿你今后永远平安。”
阿列哥的身体虽已与茨冈人为伍,但他并没有走出自我的藩篱,也就很难改变文明的偏见和人性的弱点——“一个习惯于安逸的人,不可能把自由永远爱恋”,不懂得予人自由的人当然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诗人超卓的清醒和洞察力在于,他既质疑现代物质文明下的“自由”,又以同情态度重新审视茨冈人的生活——
“但你们也没有什么幸福/天地间的可怜的子孙们……/而在破烂的帐篷下/定居的也只是痛苦的梦/你们的飘泊无定的屋宇/荒野里也不能避开穷困/到处是无可逃躲的苦难/没有什么屏障摆脱命运。”
普希金雕像
显而易见,茨冈人的生活并非想象的那样自由浪漫,其精神或可随心高飞低翔,可物质性的肉体却不能不受制于外在条件的限囿——永久漂泊或许确已沉淀为血脉里的习性,但也很难说不是一种无奈,何况还有如影随形的贫困,定居文明的歧视、驱赶以至杀戮——“到处是无可逃躲的苦难,没有什么屏障摆脱命运”。
4、无处流浪或不再流浪
失去土地家国的吉普赛人餐风饮露,流浪千载,因其“无根”屡遭其他文明的歧视打压。15世纪后期,一些国家施行限制措施,颁布了不少带迫害性质的法令条例(二战期间有50万人死于纳粹集中营),毫无安全感可言的吉普赛人只能无休止地流浪。
20世纪后半叶,吉普赛人开始以组织形式为自己维权——1965年,罗姆人国际委员会和芬兰的罗姆人文化中心成立;1971年4月8日,首届世界茨冈人大会在伦敦召开,来自30多个国家的茨冈人代表决定成立国际茨冈人联合会;2004年6月,匈牙利选出了欧洲议会里的第一位罗姆人议员;次年,东欧七国发起“容纳罗姆人年代”倡议,呼吁改善罗姆人的政治经济权利和生存状况。
国际茨冈人联合会
现代吉普赛人的生活其实早就发生了巨大改变:据信有占四分之三(另一说为十分之九)的人过上了定居生活(多在条件极差的棚户区),也有小部分人仍试图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只不过他们的大篷马车/牛车变成了房车或带大篷的汽车/拖车,家畜贩卖被二手车的出售替代;锅盘修补业遭淘汰后,某些城市吉普赛人学会了汽车的保养修理;此外,流动马戏团的驯兽师,娱乐场所的小吃摊贩和算命仙也是他们常用的谋生手段。
当代吉普赛人的生活
然而总起来讲,吉普赛民族的生存状况依旧堪忧:就在近一两年间,英法德捷克等国政府驱赶外籍吉普赛人,拆除其非法定居点的行为仍不时牵动大众的神经——尽管政府一方意在整顿社会治安、规范非法居留,但此类方式粗暴且实质上有歧视特定族群之嫌的做法,难免会引发国际社会的质疑。
“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艺术,我们的传统服饰,都被偷走了,在世界各地的演奏厅和博物馆里,它们被当作西班牙、匈牙利、捷克、法国的文化演奏着、展示着,我们几百年来所有的创作都被偷走了,而我们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被人称为‘小偷’。”
——这段文字来自加拿大作家罗纳德·李《天咒的吉普赛人》,他如此愤激地批评主流文明对待自己民族的不公,而这样的不公在当今并无显著改观。
西班牙塞维利亚弗拉门戈舞蹈团经典舞剧《卡门》
吉普赛的舞蹈
缘自全球一体化大潮势不可当的冲击裹挟,这个数百年来四海为家的民族不仅最基本的生活方式、谋生手段发生着重大改变,其族内通婚以保存自身血统的森严关隘也已渐次失守。未来的某一天,吉普赛人也许将无处流浪或不再流浪——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多元的人类文明生态本来就面临危机,处在持续的同化与消亡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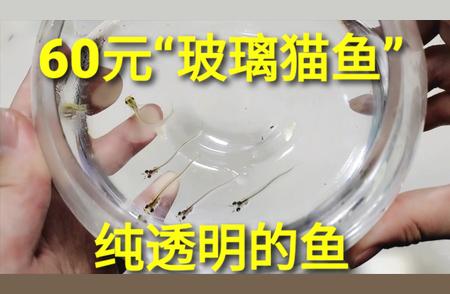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1616号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1616号